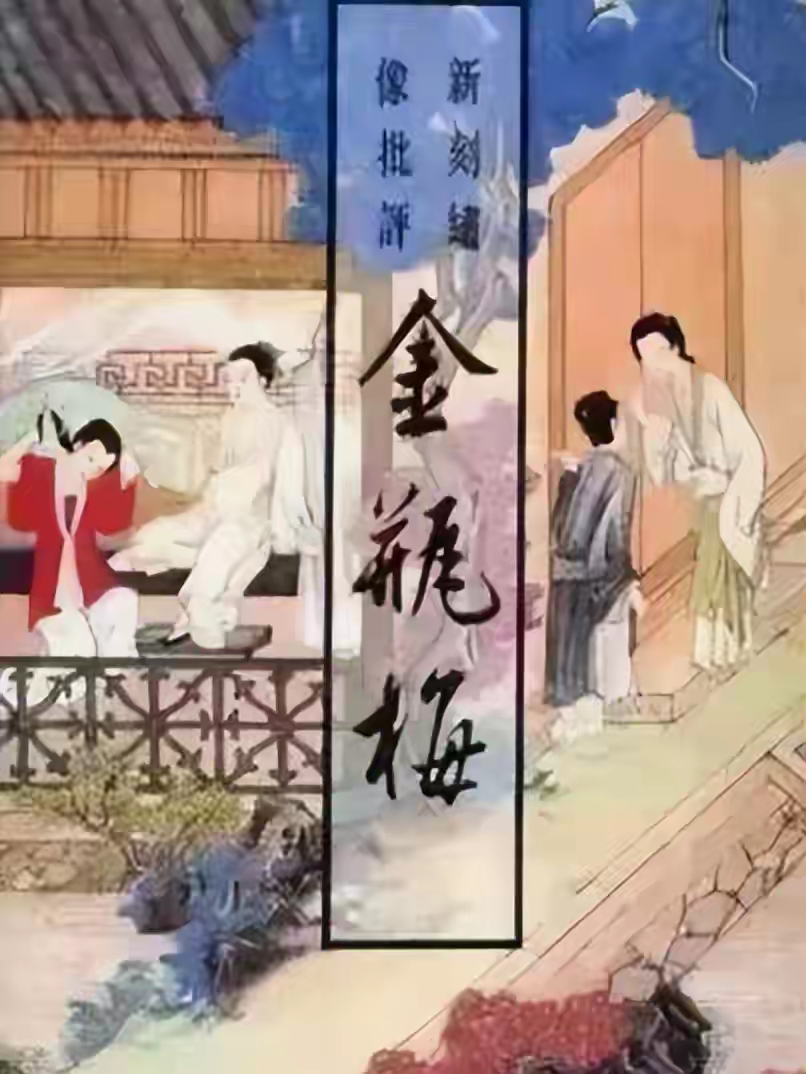
《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普通人物为描写对象,以家庭琐事为描写内容的小说,它精确而又细微地描绘出了一幅明代社会的风俗画卷。
但它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更是争议不断,被打入禁书行列。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的拍板下,《金瓶梅》才得到了小范围的解禁,毛主席将这本书当作明朝的真实历史去读,还曾号召各省委书记去看。
那么,《金瓶梅》到底是一部怎样的文学作品?它成为禁书仅仅是因为里面用大量的“污言秽语”去对性进行描写吗?作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这本书,到底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呢?它又是如何从“禁书”中脱离出来的?
禁书“禁”并不完全是“性”
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下,追求“君子”的理想人格,摒弃“小人”的自私人格,是人们的终极目标。
为了成为真正的“君子”,人们不惜竭力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欲望不仅仅是指贪婪的索取,还包括一些人性使然的诉求。
儒学在宋朝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期,“程朱理学”应运而生,“存天理,灭人欲”成了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
为了“灭人欲”,人们只能努力抑制自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凡是有不符合“天理”的诉求滋生出来时,他们只会感觉到羞耻。
性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可也是“人欲”的一种,为了“灭人欲”,必须要抑制性欲,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性是很忌讳的话题,即使无法抑制,但也只能压抑在内心深处,而不能揭露出来。
而《金瓶梅》却在这样的环境下横空出世,无疑是平地惊雷,在所有人对“性”这个话题讳莫如深的时候,这本书用将近两万字描写了一百多处男女媾和之事,语言露骨,丝毫没有避讳。
即使书中除了性的描写,还涉及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但很多读者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污言秽语”上,只觉得这是一本不堪入目的“黄书”,让人感到羞耻。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性是洪水猛兽,会让人堕落,会败坏社会风气,《金瓶梅》中赤裸裸的性的展示更是会对人心,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是它被禁的直接原因。
除了性,人心和人性也被《金瓶梅》揭露得很彻底,在作者描述的成年人世界里,“好”与“坏”是不能将不同的人进行区分的,人性是复杂的,人心是难测的,根本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坏人”。
这样的世界没有黑白之分,没有善恶之分,是灰暗的,压抑的,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迫不得已,为了生存,人心最深处的东西被一点点挖掘出来,真实而又无望,这本书揭开了旧社会的伤疤,这种痛是大家不能承受的。
同时,《金瓶梅》还向人们展示了封建官僚和地主们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和丑态百出的泼皮无赖和市井混混。
整本书几乎完整揭露了封建王朝最肮脏龌龊的一面,这是执意宣传盛世繁华的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自然不能任由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书籍肆意流通。
于是,在多种因素的加持下,《金瓶梅》便成了“禁书”。
“性”外衣下的真相
《金瓶梅》虽为“禁书”,但却屡禁不止,在下面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有些是因为猎奇,有些人却是在通过书“污浊”的外衣,看透了这部作品所描绘的真相。
首先,虽然书中关于情色的描写太过露骨,但这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也不是为了供人享乐而刻意强加进去的。
《金瓶梅》所描绘人物的性状态是一种纯粹的性欲,这种欲望仅仅是停留在生理层次上,是不夹杂任何感情的,所以这些描写很是放纵和夸张,感官冲击力很强,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人物的病态和扭曲。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只允许上流贵族阶层的欲望肆无忌惮,而普通人的正常人性却要受到他们野蛮的镇压,甚至连生存的权力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了性禁忌社会,人们认为性是不纯洁的,有性欲望是羞耻的,是罪恶的。
但是,人的天性是抑制不住的,不管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会通过各种形式展现出来的。
越是压抑,人们就越是偏执和向往,性欲实现方式也变得病态和丑恶,这是压抑人性导致的结果,是无法制止的。
所以,《金瓶梅》中描述的不管不顾,极致享乐的性场景是有理可循的,是人们长期处于自南宋以来“程朱理学”下对性和欲望的压抑状态下的一种反抗,有道是,越是去抑制,旧越是抑制不住。
另一方面,这种病态性爱方式的描写,也反映出了底层人们对享乐的追求。
可同时本书也旨在告诉人们过度去追求享乐这是不现实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书中的西门庆死于自己的享乐欲望,李瓶儿为了争宠而身亡,潘金莲也因为贪欢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书中的人物为了追求极致的享乐而摒弃了所有的伦理道德,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但最后却都因此而亡,这就是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残酷,是充满悲凉色彩的。
在鲁迅先生的眼里,《金瓶梅》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金瓶梅》不加修饰的,如实的写出了一个缺乏伦理的,矛盾的世界。
正是因为这种对性的不加掩饰的描写和对社会人性的探讨,导致《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始终作为一部有争议的作品流传于世,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然而仅就文学艺术来讲,它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是被大众认可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与众不同的,反传统,反道德的文学作品存在,才将文学创作的重重枷锁撕开了一个口子,拓宽了文学创作自由发挥的空间,后来问世的《红楼梦》中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和对自由的渴望,很难说里面没有《金瓶梅》的影子。
禁书“解禁”路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带着污名,据学者高洪钧查证,《金瓶梅》在万历三十年,即1611年就被礼部颁发的《钦定教条》列入了“禁止私刻”的名单,很多文人学者都对其避之不及。
在清朝康熙年间,《金瓶梅》虽然还是禁书,但封禁有所松动,康熙曾吩咐臣子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刻印出来,但也只能在内务府流通,坊间还继续禁制。
但禁令并没有让在坊间流通的《金瓶梅》彻底绝迹,很多人还是有机会研读这本书,著名批评家张竹坡在研读了《金瓶梅》之后,对其文学价值给予了高度赞扬,在评判这本书时也不乏溢美之词。
张竹坡赞颂《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并引领清朝文人争相阅读《金瓶梅》,一时间,这本“禁书”在文人学者之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浪潮。
虽然禁得不彻底,但《金瓶梅》毕竟背着污名,热度并没有很高,这本书真正被大众熟知,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7年,毛主席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金瓶梅》可供参考,还鼓励各省省委书记去看。
几个月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书《新金瓶词话》为底本,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发了两千部,并注明:“本书影印目的,在供古典小说研究者参考。”
刚开始,这本书的发行极为严格,发行对象仅限定为副部长,省委副书记以上,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知名正教授等文化界名人,而且所有购买此书的人都会进行登记,并赋予编号。
到80年代,允许出版社编审以上人员可以购买,1991年,规定购买《新金瓶词话》的人必须是副高职称以上,还需要拿着单位的介绍信,证明自己购买书籍只是出于学术目的,承诺不会向海外出售。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戴鸿森将书中将近两万字的性描写彻底删除,并对书中的章节,段落和标点进行了修改,准备发行全新版本的《金瓶梅词话》。
1985年,经过删减后的金瓶梅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完成印刷,不仅增加了印刷数量,还扩大了发行对象的范围,但还仅限于高干人员,因此这个版本的《金瓶梅》被称为高干本。
除了高干本,《金瓶梅》在印发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评本校点本,洁本,崇祯本和校注足本,其中,只有崇祯本一字未删,其它版本都是进行了删除和修改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开始在市面上流通,也不再限制发行对象,研究此书的学者越来越多,它的文学价值也被一点点挖掘出来,这是《金瓶梅》的幸运,也是文学界的幸运。
结语
禁《金瓶梅》禁的是人性,禁的是人欲,禁的是人的觉醒,禁的是人们对旧社会人性欲望的认知。
但这些却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一样,是禁不住的,所以《金瓶梅》才会顶着“禁书”的名号一路披荆斩棘,冲破禁忌,闻名于世。
很喜欢学者东吴弄珠客曾说的一句话:“读《金瓶梅》而心生怜悯者,菩萨也;心生惧心者,君子也;心生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芸芸众生中,超凡脱俗的人并不多,大多还是俗人,读《金瓶梅》时,万万不敢效法,却难免会心生欢喜,要想生出怜悯和惧心,还需具备一双“慧眼”,透过“污浊”深究背后的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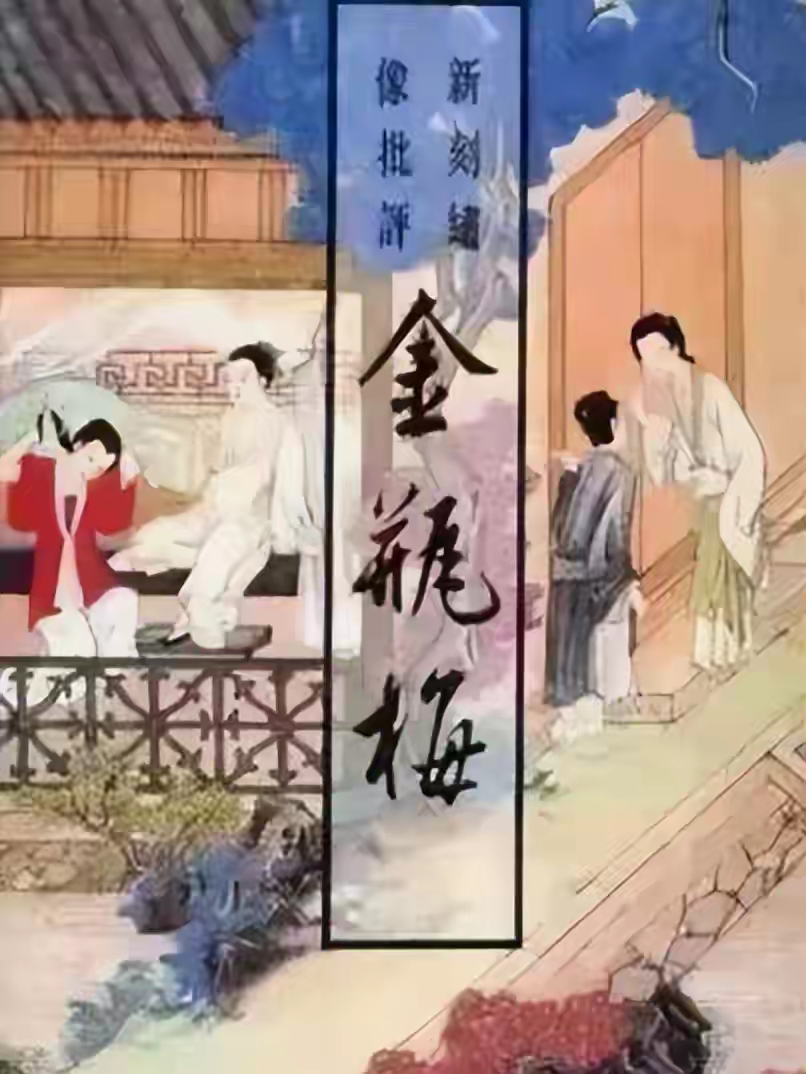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